“李寄斩蛇”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特别是通过小学课本和连环画的传播,让无数人都留下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一位无畏的英雄少女,机智勇敢地斩杀了蛇妖,最终既救了自己也救了许多孩子。
然而,问题在于,最初记述这个故事的,却是一位坚定的有神论者,那他为什么要赞颂一个无神论的小英雄破除迷信呢?

干宝的世界观
在《搜神记》原序中,作者干宝明确宣称著书的目的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鬼神之存在不仅不可否认,他还力图证明这一点。
全书二十卷,多系怪力乱神,这些长期被视为糟粕,但其中若干篇章到了近代以来又被抽离出来加以全新解释,例如一些不怕鬼的故事,以及卷十九的这篇《李寄斩蛇》。但“不怕鬼”实际上仍是鬼故事的一种,以承认鬼的存在为前提。同样,他记述《李寄斩蛇》不可能是为了宣扬无神论,倒不如说,在他的世界观中,超自然事物并非人不可胜。
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基调一致,即鬼神或生物精灵与人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它们是与人类平等、相关的实体,只是彼此的“法力”不同罢了。不论鬼神显灵、不怕鬼乃至除灭生物精灵,其出发点都未否认它们的实有存在及超自然法力,这与我们所理解的无神论显然存在细微但关键性的差别。
《搜神记》中有多篇记录与蛇有关的异兆,这些异兆所体现出来的,或为祯祥,或为灾异,但时人莫不怀有敬畏之心。相信大蛇具有超自然力,是当时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且杀蛇的后果也未必像李寄那样成为英雄,反倒有时招致大难。如卷十二载廖姓巫蛊世家,因为新妇误杀家中大蛇,举族遭受灭顶之灾;卷二十载陈甲在海盐县沼泽中射杀大蛇,三年后遭报应身死。考虑到海盐县是干宝本人生长之地,此事可想是他根据乡里传闻写成,纪实的准确性更高。如果他记载李寄斩蛇的事迹是旨在破除迷信,那就很难解释他在这些篇章里又“宣扬迷信”。
在干宝的世界观中,生物长寿者均有超自然力,其意图兼有善恶——确切地说人是不可知的,但在其表现为妖邪时人也可以法术或正气制服之。正因为神灵的意图不可知,因此人有必要向其祈祷、施行贿赂,以祛除灾凶及惶恐不安的心理。
《搜神记》中两则故事都表明:祭祀可得福,否则将有大难。卷五蒋山传说,蒋子文显灵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又卷十一记载,“吴时,葛祚为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沉没,不者,槎浮,则船为之破坏。”
此种观念实为巫术献祭的必然前提:献祭、祈祷是安抚神灵,以使阴阳两界共处的契约性承诺,双方均应遵守。尽管这有时看起来像是对超自然力量的贿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献祭是维持太平生活的必要前提,而且是不得不遵守的禁忌,因为如果不这么做,超自然力量就会对百姓降下灾祸。
值得注意的是,有时神灵以蛇的外观现形。《搜神记》卷七记载晋明帝时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树中,每出头从人受食”,这在当时被视为“国有大忧”的灾难预兆。类似的故事直到五代后周时仍有:“蜀郡西山有大蟒蛇吸人;上有祠,号曰西山神。每岁土人庄严一女置祠旁,以为神妻,蛇辄吸。将不尔,即乱伤人。周氏平蜀,许国公宇文贵为益州总管,乃致书为神媒合婚姻。择日设乐,送玉女像以配西山神。自尔以后,无复此害。”(《太平御览》卷八八二神鬼部二引《郡国志》)
这两则故事,与李寄传说的前半段有着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后周蜀郡西山的蛇神/山神,与李寄的事迹在时空距离上都很遥远,可见那不是一时一地的特殊信仰,而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
蛇崇拜
中国南方各族存在普遍的蛇神崇拜,上古记载中尤以东南夷为显著。上古虫、己、巳、蛇丘、虺等地名可以与东夷、淮夷以虫、蛇为图腾的各分支的文化遗存相互印证,说明虫、蛇图腾实为夷人崇拜的主要目标之一。虫、蛇、它三字本出一源。《说文》训“它”为虫,段玉裁笺疏说虫、它:“二篆实一字也。”《山海经·海外南经》:“虫为蛇。”汉字“祀”似也系蛇崇拜的象形字:祭祀是与“巳”相关的。
蛇多在山间穴居,古人以为山生云气,主降雨,形成山神司雨水的观念,蛇常兼为山神和雨神。《玄中记》:“夫自称山岳神者,必是蟒蛇。”《景德传灯录》卷四:金陵牛头禅第三世慧方将入灭时,“感山神现大蟒身”。蜀郡西山神也正是蟒蛇。
又《搜神记》卷十八伪托董仲舒语:“巢居知风,穴居知雨。”穴居的蛇可想被认为知雨,一如凤鸟图腾与风有着密切联系(鸟巢居知风)。这又与上一点或存有内在联系:因为在原始人看来,云雨等天气现象与性一样,同为阴阳交合的产物,故此古代天文学有时与性学密切关联,“云雨”一词在汉语里也别有含义。向蛇神献祭少女的巫术原理或许正在于此。
山神还同时是司生命之神。中国人之所以相信“魂归泰山”,就是这一传统的遗绪。武珪《燕北杂录》记载辽代祭祀之俗:“戎人冬至日杀白马、白羊、白雁,各取其生血代酒,戎主北望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为黑山神所管。又彼人传云:凡死人悉属此山神。”虽然祭祀的做法不同,山神形象也各异,但这种信仰本身的基底是类似的:人们相信,死后的灵魂将由超自然力量所接引,进入天界。
在古希腊的阿赫托弗里亚节庆典中,人们将制成蛇和菲勒斯形状的糕饼投入一个坑洞,那与大地受孕秘仪有关,那些峡谷、地缝、裂罅还被看作是通往冥界的入口,甚至还有这样一个古老的希腊习俗:将少女们送进毒蛇盘踞的山洞以检验她们的贞操。如果他们遭了蛇咬,就说明她们不再贞洁。心理学家荣格指出:“每年向龙献祭一名少女,在神话学层面上,恐怕是最理想的一种祭祀。为纾解恐怖母亲的愤怒,最美丽的少女作为人类强烈邪欲的象征被送上祭坛。”
人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种献祭对当地社会的凝聚是必要的,因为在信奉巫术的先民心目中,蛇神不仅是令人敬畏的超自然力量的化身,而且提供了必要的守护:所谓“神守之国”,意味着这片土地的安宁是有保障的,而人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定期向它献祭。
据《史记·孔子世家》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后汉书·张衡列传》李贤注引孔子语时又有“山川之守,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的说法。中原文明中将这类祭祀山川的活动变成王者垄断的特权,正可见兹事体大,不能由民间任意为之。这一观念到后来演变成城隍崇拜和土地神崇拜,其形象也变得更像是帝国秩序中的守护一方国土的下级官吏,但其精神内核没有改变,那就是相信一方山川土地是有神秘的超自然力量镇守的。
无论从民俗、神话的研究,还是百越文化的历史考察来看,被李寄所斩杀的蛇,起初应当是受当地人崇拜的对象。人们向它献祭人牲,正是因为对它赐福祸能力的确信。从它穴居深山沟壑中的情况来看,至少无疑被视为山神和司雨神,而其作为穴居动物的地下形象,也与大地的神秘力量和人类繁衍的性秘紧密联系。
然而,这种观念终于遭到了严峻的挑战。
新旧冲突
自秦以降,明确的蛇崇拜界线逐渐向南退却,最终成为汉人眼里南方蛮夷的异俗。《说文》:“闽,东南越,蛇种。”“蛮,蛇种。”“闽”字,门中有虫,意指上古闽越人以蛇虫为图腾。东南的瓯越、闽越是确凿无疑的蛇图腾氏族,但其巫鬼传统在西汉时受中原文明影响,也开始逐渐没落;也许在越人看来,正是因为受汉人影响而怠慢了鬼神,才是本族衰耗的根源:《史记·封禅书》:“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在历史上面临文化冲击的危机中,各族都有过类似的想法。
李寄故事并无确切的年代,大致应在三世纪末的西晋时期:《搜神记》的书写惯例,凡有确切年代的系前朝,而只写故事发生地点的则多系作者同时期的事。当时李寄所在的闽中,仍被视为蛮荒异域,在干宝的观念中,这样的地方多怪物——《搜神记》卷十二:“中土多圣人,和气所交也。绝域多怪物,异气所产也。”
东南各省以福建开发最晚,两汉始终只有一个东冶县,极少派驻军政人员。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许靖从会稽浮海往今越南北部的交州,自称“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当时航海都是沿海岸线行进,显然在中原人眼里浙闽一带仍属未汉化的蛮夷之地。孙氏占据江东后,孙策才遣贺齐等平定闽西北一带:建安元年(196年)进占东冶,但建安五年闽西北的建安、汉兴、南平三县反抗还未平息,建安八年才“复立县邑”。据此不难想象,当时本地土著对汉人势力的渗透曾有过长期的抗拒,所以才如此一波三折。
孙吴割据江东,为谋三分天下进而争霸全国,因成中国史上第一个倾全力开发东南的政权。其在人力开发上包含一体之两面:即掠夺山地土著青壮导致当地人口锐减、及汉族武装殖民的推进。257年赣东抚河流域同时设置五县及临川郡,260年乃在闽西北设置昭武、将乐两县;而赣东向闽西北富屯溪、金溪流域的移民定居自213年已开始。在李寄故事的末尾,“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指其父为将乐令”,这从历史来看有几分时代错置,毕竟汉武帝征服闽越后,闽中本已无越王,他也许是地方诸侯,已非闽越本族之王。但不论如何,李寄那时是在将乐已设治,福建各县建置年代可体现其开发、汉化的进程,如果假定李寄生活在3世纪末期,则她所属的将乐县正处在闽越地区汉化浪潮的最初三四十年,且正是其前沿地带。
这一敏感的时期和地点,无疑给当地带来冲击性的剧变。按中原王朝一贯的边疆政策,这些前沿新县通常“因其故俗”,不征赋税;但会接纳一些逐步汉化的土著任低级官吏。通常而言,这一汉化的浪潮一旦开始,就是不可逆的。但初期汉人很少,西晋初福建各县人口平均仅三千。在这遍布森林的崎岖山区开发农业进程缓慢,至初唐当地仍有很多非汉族血统。然而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在这一边缘地带,存在着一种可以想见的漫长文化冲突。
在李寄的故事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首先,她和父亲(李诞)都拥有汉名。对于立县不到半个世纪、人口不足三千、刚开始汉化进程的边疆小县,这是耐人寻味的。其次,她在与父母的交谈中提到“缇萦济父母之功”,如果这并非作者干宝添加,而确实是李寄本人原话,则表明她居然还能引用西汉的这一典故。最后,往常被献祭的九女都系婢女或罪人家女,出身社会底层。李寄家庭的社会身份如非汉人移民中的贫民,也是初染汉化的当地闽越人。但无疑,他们对蛇神的感觉可能憎恨更大于畏惧,或更确切地说,畏大于敬。如果他们是汉人,那么对蛇神的敬意就更淡了,因为对当地人不可侵犯的圣物,对一个外人来说,常常却是一件不会引起任何敬意的物品。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就能杀死的大蛇(不论她的英勇机智受到多大的夸张),当地成年人不可能真正对它束手无策,只是他们的行动一直受限于一种巫术上的敬畏心理:换句话说,他们畏惧的是巫术的神秘力量,而不是蛇本身。
历代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带确立统治后,通常最重要的就是着手建学校、移风易俗,由一批循吏来完成。这种德政换个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一种殖民教育。每逢当地文化观念与汉文明观念冲突时,常常以后者的获胜告终。如明时期汉人“贞洁”观念传入云南峨昌地区后,与当地原有的收继婚产生严重冲突;结果转房习俗被看作陋习而逐渐被革除。作为一个无文字的社会,当时闽越的状况深合这句民俗学上的名言:“一个民族的神话系统通常即是它的教育系统”。而今对神圣意义的解释权落入受汉文明影响的人手中,这一教育系统随即加速了它的崩溃。用人献祭不管在当地闽越人看来如何神圣,对当时的汉人来说都是骇人听闻的;犹如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后也极厌恶地禁止了阿兹特克的宗教祭祀。
参照一下西方神话的情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常有巨蛇(及其升级版巨龙)守护着洞穴世界中的宝藏,但当基督教兴起之后,它们就成了有待破除的迷信。荣格在《英雄与母亲》中征引公元5世纪末罗马的圣西尔维斯特(St. Sylvester)传奇:
“在矗立着朱庇特神殿(the Capitol)的塔尔培亚山(Tarpeian Hill)中,曾生存着一条巨龙。每个月都有魔法师率领那些生活不检点的少女们去祭拜它。他们沿着山洞的365级台阶走下幽深的洞底,像是通往冥界一般。他们携带着各种祭品和意在洗涤罪孽的供品,去饲喂这条巨龙。接下来就会看到,巨龙猛然起身。它尽管不出洞,但它的呼吸毒化了空气,致人死亡,孩子们的死更是引起人们极大的悲伤。因此,当圣西尔维斯特为捍卫基督教义与异教徒论战时,异教徒们便向他提出挑战说:西尔维斯特,你何不下到那巨龙的洞窟去,凭着你那上帝的名义降伏了它呢?哪怕叫它只安生一年也好,也能少害些人命啊。”
另一篇佚名作者写于公元5世纪的《应许》(De promissionibus)提到了一则极其相似的传说:“在罗马城附近的一座洞窟里,有一条可怕的巨龙。这是一架机械装置,龙口中有宝剑飞舞,两只龙眼是由闪闪发光的红宝石做的。每年人们都选派少女,按宗教仪式洁身后用鲜花装饰好身体,献给巨龙做人祭。当她们携带供品走下石阶时,会在无意中触动那恶龙的启动机关,龙口中的宝剑当即弹出,将她们刺穿,无辜的鲜血洒在地上。有一位以德行高尚闻名于罗马贵族、摄政官斯提利科(Stilicho)的修士,他以下面的方法摧毁了那条恶龙:他用一根竿杖和自己的手小心探索每一级台阶,摸清了那可怕的机关所在。随后,他迈过那级有机关的台阶,下到洞底,砸毁了那条巨龙,把它劈成碎块。借此告诉当地人,他们所敬拜的不是真正的神,而是一件人造物。”
在荣格看来,这一幕象征着英雄战胜了自我:“英雄从黑暗洞穴中取回的宝藏就是生命:那正是他自己,一个刚刚从无意识的黑暗的母性般的洞穴中获得新生的自己。在那里,他曾受困于力比多的内倾或退行而难以自拔。……而当他从母体中再生降世之时,他就成了征服巨龙的英雄。”根据这一心理学分析,蛇“是无意识的绝佳象征”,而“作为一种极为古老的原型心理结构(psychologem),英雄代表着积极的、正性的、为人赞赏的无意识活动;而龙则代表着消极的、负性的、人所不喜欢的无意识活动——不是生育,而是吞噬;不是建设性的有益行为,而是充满贪欲的滞留和毁坏。”
无论是从什么意义上说,被杀死的蛇神都象征着基于非理性基础上的原有信仰被压制,新的文明和理性意识从这一混沌世界的死亡之中诞生。一种迥然不同的新秩序出现了。
从蛇神到蛇妖
要理解李寄斩蛇一事背后所隐藏的历史性社会变迁,我们就必须先重新理解这一故事的种种象征意义。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曾说:“一些高等文明的神话材料传到我们手里已是孤立的文学记载,没有实际生活的背景,没有社会的上下文。这就是古典神话和东方已逝文明的神话。在神话研究方面,古典学者必须向人类学家请教。”
从人类学的观点看,很多被妖魔化的动物,起初都曾是受崇拜的对象。乌鸦在古代北欧神话中是一种神圣、尚武且无所不知的神鸟,但它在基督教中的形象却是邪恶的,加上它在异教占卜中的作用,总是被归入属于魔鬼的动物。直到12世纪,熊在欧洲各地得到普遍崇拜,它不仅勇武,且有野蛮的性感魅力,有些贵族声称自己祖先是“熊之子”,是妇女被熊掳掠强暴后所生下的后裔。这引发了基督教会的恐惧和厌恶,圣奥古斯丁宣布:“熊就是魔鬼。”它所冬眠的洞穴,也被教会看作是阴暗隐蔽的黑暗国度,那就是地狱。在这种情况下,“熊被赋予了无数的恶习恶行:粗野、邪恶、淫欲、肮脏、贪食、懒惰、暴躁。这样,曾经受到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极度崇拜的百兽之王,就慢慢地变成了地狱生物的首领。”
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萨本是雅典娜的原型;雅典娜变成了美丽的贞女,同时也杀死了她的原型——狰狞可怕的蛇发女妖。亚洲内陆的独眼巨人崇拜,也曾是人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供奉”的既敬又畏的崇拜象征,但后世对人生命的珍惜以及对可怖形象的厌憎,终于使独眼巨人蜕变成一个吃人恶魔的形象。这种狰狞可畏的形象曾经代表崇拜对象的强大威力(藏区神灵至今仍多形象恐怖),却逐渐难以为后世所接受,神灵的形象逐渐由半人半兽过渡到人类的形象。英雄神话在从无意识分离后出现了独立的自我,英雄变成了打败怪物的人。
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家弗拉基米尔·普罗普在《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中着重指出:“与蛇妖作战的母题产生于吞食的母题并且是积累而成的”,蛇妖起初是蛇神,它本身具有两重性:“好蛇妖、作为惠赠者的蛇妖是蛇妖的初级阶段,后来它转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蛇妖最古老的形式,即充当吞食者的蛇妖”,在这里,吞食最初是一种授礼仪式,赋以青年人(未来的巫师)以神力,通过这一成人礼的就是伟大的萨满。在完成蛇神到蛇妖的转变后,情形发生重大转折,“如果说先前主人公是被吞食的对象,那么现在主人公就成了消灭吞食者的人。……重心向英雄主义的转移,为这个神话的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新现象做了准备。”
从神话叙事学的角度来说,李寄斩蛇的故事符合流传广泛的“杀死怪兽母题”。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发现,“在50种文化中这一主题出现在37种之中,其分布地较集中。在北美和太平洋岛屿等地出现较频繁”,但与李寄故事不同的是,这一主题常具有明显的俄狄浦斯意味,例如非洲班图人地区常见的是,怪兽吃掉了一位女性的丈夫,她逃脱了,不久生下一位英雄,很快长大成人并杀死一只或多只怪兽(除了他生父),拯救了人民,并成为国王。根据另一母题:儿童被卖给(许给)魔鬼,一旦孩子“被预言要许配给怪物时,以后的每一事件,都是以他怎样逃避怪物的力量为枢纽的”。故事中李寄是小女,还有姐姐,这也符合民间故事的规律之一:英雄常常是排行较小的孩子。
因此,李寄的事迹之所以“其歌谣至今存焉”,可能有两种意味:一是这一故事符合民间故事母题的结构,得到广泛流传;二是李寄取代蛇神,继承了它的神秘力量。在一个巫术崇拜的人群看来,李寄之所以能杀死大蛇,不是因为她的机智勇敢或大蛇迷信的虚妄,而是因为李寄本人具有压倒大蛇的神秘力量。李寄杀死蛇神,一如雅典娜杀死狰狞的美杜莎,标志着人形的蛇女神对蛇神的取代。新的女神将接管蛇神的超自然力量,而蛇本身则受到妖魔化。
干宝声称,在李寄斩蛇之后,“自是东治无复妖邪之物。”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斩蛇不是蛇崇拜的终结,而只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闽地的蛇神崇拜最终通过一个全新的转变,还是保存了下来,其共同特点是被崇拜的对象全部被人形化。同样地,土家族等南方民族也曾经历由白虎图腾向人文祖先崇拜的过渡。
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新的蛇女神以新的面貌在闽中出现:此即闽东北的民间信仰临水夫人陈靖姑。据说她于唐代宗时生于闽侯下渡,曾坐化成神降伏蛇精而受封临水夫人。供奉于古田临水殿,为著名救产护卫神,也是闽江船民和福州出海舟子的主要救护神。这个女神/女巫形象与李寄一样,从小就表现出神异的一面,而她的崇拜核心地点古田,可能也与李寄故事中大蛇的地点邻近。
由百越先民的蛇神崇拜演变而来的神灵信仰在华南汉民社会中广泛存在。南平樟湖坂有蛇王庙,供奉的“连圣公”其实就是连姓蟒蛇精,每年七夕“蛇王节”都举行“游蛇”。另一种变形则是蛇神化身为人形神的助手,如福州五灵公的“四季将”瘟将中也有一“蛇将”;漳州三平祖师公有一“蛇侍者”,传说唐武宗时漳州有蛇妖,被僧人杨义制服后为其侍者,行善事成神,被称为“侍者公”。
还有“九使蛇神”传说:唐僖宗时福清黄檗山有巨蟒为害,邑人刘孙礼妹三娘被捕入洞为妻,刘出游得异人传授后归与蟒斗法,时其妹已生蛇郎十一,刘怒杀其八,其妹拜求,余下三子遂为神,即九使(英烈王)、十使(昭应王)、十一使(光济王),他们保佑渔民,护航救难、能退海寇,多有灵验,因而九使信仰在闽江口一带民间信众甚多,并由渔民播迁至霞浦、福鼎一带。现在长乐潭头镇厚福村每年正月初十“游九使英烈王”仍是福州地区最盛大的游神活动之一。更为特别的是,那个蟒蛇精也受刘孙礼感化,后来改邪归正,终于修成正果,号“蟒天洞主”。后来明初长乐人马铎累试不第,它还化身老者指点迷津,让马铎得以高中状元,马铎上书晋封其为“蟒天神王”。如今,它在长乐等地也香火鼎盛,刘三娘尚配祀其侧,称为“种痘夫人”。
凡此等等,均可看出,蛇神的命运可以有不同的走向,这种传统的演变,不一定是骤然断裂的,也可能是温和的过渡。固然,如果没有汉文明的渗入,蛇神也还是会迟早转化为蛇妖,并被人形的蛇神所取代,但也许就不是这样像李寄斩蛇那样猛然的断裂。但不论如何,他们所代表的那种超自然力量,不会随着它们被杀死或驯化而消散,因为说到底,民间社会仍需要它。
现代人把李寄斩蛇的故事看作是歌颂那个少女破除迷信的大无畏精神,才是与传统的真正断裂。正如民俗学家阿兰·邓蒂斯所言,“……为了宣传的目的而重新整理民俗,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民俗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和武器”,古老传说中表现的民俗转变与人神斗争为政治的目的而加以整理。每一个人的目光就聚焦在那个少年女英雄的身上,为她表现出来的超前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反迷信勇气而感动欢呼。但如果认为这就是全部事实,那就只能证明我们实在遗忘了太多东西。
参考书目
1、干宝《新辑搜神记 新辑搜神后记》,李剑国辑校,中华书局,2007年
2、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3、《葛剑雄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4、[瑞士]C.G.荣格《英雄与母亲》,范红霞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
5、[法]帕斯图罗《色彩列传:黑色》,张文敬译,三联书店,2016年
6、[俄]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贾放译,中华书局,2006年
7、[美]阿兰·邓蒂斯(Alan Dundes)编《世界民俗学》,陈建宪、彭海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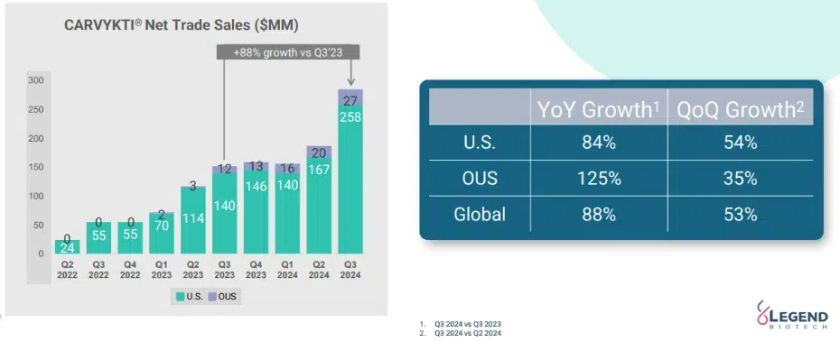




 蜀ICP备2022028980号-1
蜀ICP备2022028980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