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插曲
1995年1月17日星期二清晨,日本第五大城市神户发生了一次大地震。 超过15万栋建筑物倒塌,6000多人丧生。正如丹尼尔·奥德里奇(Daniel Aldrich)所说,这场地震展现了城市中不同社区在灾难准备和响应速度上的巨大差异。以活跃而闻名并被学者纳入研究的马诺(Mano)社区[1],在地震发生后不久,居民们便自发组织救火队伍开始灭火,而在与马诺临近的其他社区,居民们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街坊邻居的住宅烧成灰烬。地震发生之后,马诺社区邻里协会协助救援行动,把无家可归的居民疏散到附近的学校,搭建社区厨房,并组织守夜人保护被遗弃在废墟里的居民财产。在重建阶段,这个邻里协会协助检查受损的建筑物。他们每周发布时事通讯,让社区居民了解灾情,并帮助监督改造受损房屋。像马诺这样社区的居民会比其他社区的居民更快投入到灾后经济重建工作中。在神户大地震以及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其他灾难中,决定死亡人数差异的因素不仅仅只局限于灾难的物理层面(例如地震震级),还包括人类自身和社会层面的因素。
印度社会周期性地受到印度教和穆斯林教之间的族群冲突的破坏。然而,正如瓦什尼(Varshney)所言,穆斯林教徒与印度教徒在城市地区的分布比例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城市长期遭受种族暴力,而另外一些则成功地维持了族群和平。这些城市维持族群和平的秘诀是什么?阿什图什·瓦什尼(Ashutosh Varshney)的答案是,这类能够维持族群和平的城市通常有民族融合的民间组织。瓦什尼猜测,这种组织成员中既有穆斯林又有印度教徒的民间组织(商业团体、贸易工会,甚至是当地图书馆的阅读圈),是保持各族群之间有效沟通的手段,并有助于遏制煽动者经常在社区内传播煽动民众骚乱的谣言。
这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小插曲具有什么神秘的、共有的社区特征呢?显然,社区结构要素(以先前存在的社区组织的形式)帮助居民迅速从自然灾害中恢复(日本的例子),并避免族群冲突(印度的例子)。居民之间的这种关系网络构成了他们所居住社区的社会资本的一部分。

电影《教父》剧照
社会资本的定义
社会资本的一个简单定义是“个体作为一个网络或一个群体的成员而获得的资源”。事实上,很难定义社会资本,社会科学中存在大量的这一概念的变式。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资本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人口健康等学科。社会资本的跨学科性质使其定义变得模糊不清。但社会资本的大多数定义都强调了两个特征:其一,它是一种资源;其二,它是通过社会联系而产生的。
布迪厄在他关于“资本的类型”的文章中指出,“资本”不应仅限于金融资本领域[2]。换句话说,在人们的日常交流中,资本等同于钱,但把资本仅局限于此就大错特错了。资本可以指任何货物或资源的存量,例如,经济学家把人一生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存量称作“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布迪厄将某些习惯(例如去博物馆和音乐会)、喜好或言语和服饰的风格视作“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用来体现个体在所处社会中的象征性地位。“社会资本”意味着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可供社会成员使用的有形资源。换言之,当我们与好友一同外出游玩,在享受美好时光的同时,我们也从可用的社会关系中获得了物质与精神资源。也正是如此,社会资本有时也被称为“网络资本(network capital)”。
在经济学理论中,资本有两个特点:①它需要消耗其他来创造未来的利益;②它提高了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据此我们可以推论,教育也是一种资本类型,因为:①人们为了在学校获得教育而不得不牺牲乐趣(以及收入);②学校教育提高了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例如操作一些复杂精细的小工具)(见第二章)。然而,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却认为,“社会资本”并不完全符合资本的两个特点,因为现在的人际关系并没有为了未来的利益而作出任何“牺牲”,也没有做任何有目的性的投资。虽然我们同意大多数人进行社交并不纯粹是为了工具性目的(我们和朋友一起出去玩是因为这样很有趣),但在社交过程中,我们花费了经济学家们常常喜欢提及的时间成本。当人们在民间组织(比如当地的居民协会)中进行志愿活动时,他们实际上是牺牲了现在(毕竟,喝啤酒和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更有趣)来建立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
将社会资本与健康联系起来的理论路径
将社会资本与健康结局联系起来的路径因分析层次而异。从个体层面分析,社会资本是指个体通过以自我为中心的网络获取的资源。有用信息的获取(比如哪里可以免费注射流感疫苗的消息)、工具性支持(例如现金贷款)的获取和社会强化(例如情感支持的交换),这些都是与健康相关的资源。从个体层面分析,我们有时候很难将“社会资本”与“社会支持”区分开(在第七章中讨论过)。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社会支持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强关系(至少是社会支持,通常是按照流行病学中以自我为中心的网络的方法进行评估,详见第七章)。个体社会资本也可以从强关系中获得,但更多的是从弱关系及熟人关系(acquaintance ties)中获得,例如通过资源生成法进行测量(详见后文关于社会资本测量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较于社会支持本身,个体社会资本可以被用来代表个体网络的多样性(例如弱关系、跨群体之间的桥型关系)。例如,个体网络社会资本,具有多样性,在调整了个体的强关系后,可以预防吸烟和高血压[3]。换句话说,在个体层面上,拥有多样化的社会网络似乎比仅仅从亲密关系中获得社会支持要更加有益。
当我们把社会资本作为一个群体层次的结构时,需要把它看作整个社会网络的一个属性,例如一个将社区中居民联系起来的社区网络,这个网络可以给嵌入其中的个体带来益处。当在群体层面分析时,社会资本与一组“衍生性质”相联系。在群体层面上可能与健康结局有关的三种机制值得特别关注:①社会感染(social contagion);②非正式社会控制(informal social control);③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
社会感染认为,行为在一个紧密结合的社会网络中会传播得更快。在网络学中,网络成员之间的传递性越大(网络中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系越饱和),成员影响网络中其他成员行为的途径就越多。行为可以通过信息的扩散或通过行为规范的传递而在网络中传播。有时,通过网络传播的行为可能对健康有害——例如肥胖通过社会网络的传播——但在其他时候,这种通过网络传播的行为也可以促进健康,例如戒烟的传播。在弗雷明翰后代研究中,克里斯塔基斯(Christakis)和福勒(Fowler)发现,戒烟行为服从“三级影响”(three degrees of influence)规则,也就是说,我们所做或所说的事情都通过我们的社会网络产生三级不同程度的影响。当某个体戒烟后,其直系朋友戒烟的可能性会增加60%(一级影响);同时,其朋友的朋友戒烟的概率会增加20%(二级影响),其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戒烟的概率会增加10%(三级影响)。比如在一个追踪30年的队列中,剩下的几个长期顽固的吸烟者逐渐被挤到了社会网络的外围,也就是说,他们发现自己逐渐被他们的社会交往人群所排斥。值得注意的是,“三级影响” 规则是一个群体的属性。换句话说,我们熟悉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可能不会认识我们全部朋友的朋友(二级),至于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我们认识的可能性更小。克里斯塔基斯和福勒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个社会群体中,我们会受到来自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的影响。作为网络中的一员,我们可以从群体其他人的行为中获益。如果这些关于行为影响的观点是正确的[4],那么我们必然会发现,在一个凝聚力更强的网络中(例如更多社会资本),行为会传播得更快。
非正式社会控制是指社区内的成年人维持社区秩序的能力,即当他们目睹他人的一些越轨行为时做出的干涉行为。这个概念起源于犯罪学,并被用来解释破坏行为和犯罪发生的社区差异。一个有凝聚力的社区是这样的:当社区里的青少年在街头闲逛或是从事违法活动时,居民可以依靠社区内的成年人(不仅仅是父母或正式的执法机构)来对他们做出相应的干涉。当社区网络闭合时,这种非正式的社会监督就会增加。也就是说,社区中的成年人在社会层面上是相互关联的。尽管最初发展非正式社会控制是为了解释社区抑制犯罪的能力,但现在它同样适用于预防一些健康相关行为(例如青少年的吸烟、酗酒、药物滥用)[5]。当父母在孩子不注意的时候,依靠邻居对孩子的行为进行监管时,他们就已经从所属的社会网络中受益了。换句话说,非正式社会控制是群体的一个集体特征。
集体效能是群体自我效能的类比,即指动员集体进行集体行动的能力。在本章开头提到的神户大地震的小插曲中,震前拥有较高密度民间组织的地区在灾后能更好地做好准备、更快地恢复过来。当一个社区的居民通过民间组织和志愿协会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在紧急情况下他们就能更快地动员起来。一个集体出现问题时,我们中的许多人(也许大多数人)会选择什么也不做,让别人去处理,这被称为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那么为什么人们会为诸如清理地震后的残骸等集体问题自愿付出自己的努力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已经通过现有的社区组织形成相互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做出“搭便车”的行为可能会损害自己的声誉以及受到社会制裁(例如被集体排斥)。在此情况下,来自群体内其他成员的制裁威胁便足以调动集体行动。因此,公民社区参与度可作为社区社会资本的一个粗指标。此外,一旦建立起一个目标单一(例如抵制污染)的民间组织,这个组织就可以灵活地达成其他的目的(如应对灾难)。科尔曼(Coleman)用“多功能的社会组织”一词来描述一个为某一目的而建立的协会后来却可能用于其他目的的现象。如此一来,社区组织将更有效地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
总而言之,通过上述三个过程(社会感染、非正式社会控制、集体效能),个体能够从他们所属的社会团体(如社区中父母们组成的网络、邻里协会成员组成的网络)中获益。除了社会网络相互联系的成员外,社会资本还能让网络外的个体获益,即获得集体内的一些非排他性资源(即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共资源)。例如,一位没有参加当地组织的居民仍能受益于志愿者对灾后环境的清理;工作场所中的一名员工可能因为其他同事积极参与医院的预防接种而免受流感的危害(群体免疫)。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具有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溢出效应)。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属性(例如消费的非排他性)这一点在社会资本与人口健康的情境或多层次研究中尤其受到关注(见下文)。

电影《好家伙》剧照
社会资本的消极面
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通过社会网络获取的资源被运用到好的方面或是坏的方面都是有可能的。正如金融资本可被用于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一样,社会资本也可被用于获取促进健康的资源(如牙线)或损害健康的资源(如香烟)两个方面。弗雷明翰研究发现,戒烟和幸福感在社会网络中具有传染性,肥胖和抑郁症也是如此。一些社会资本的拥戴者会因为忽视了社会资本的两面性而受到批评。社交有点像母亲们对待苹果派一样,会用一种无意识的偏见来描绘其好的一面。
波茨(Portes)在其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列出了社会资本的一些消极面,包括排斥外来者、对团体成员提出额外要求、限制个体自由以及降低规范水平。第一个消极面是紧密团结的社区往往会容易出现这些情况,因为他们会设法防止外人进入。例如,日本社会常被认为具有高度凝聚力,且日本社会的凝聚力被认为是他们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种高度团结的表象下也隐藏着许多问题。
日本社会的凝聚力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德川幕府时代颁布的一系列法令,这些法令使日本在大约两个世纪(从1633年到1853年)内一直奉行着闭关锁国的政策,直到国门最终被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的大炮强行打开。德川时代的统治者用死亡来威胁在日本领土上被捕的外国人,迫使他们过着隐居的生活。日本社会的民族同质性,以及迄今为止仍然滞留在日本移民政策中的强烈仇外心理,都是这一政策带来的影响[6]。日本社会凝聚力的阴暗面有时候会突然爆发,例如,2013年7月在山口县(日本西部)的偏远村庄三岳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谋杀案,五名七八十岁的老人在此起案件中丧生。据警方报道,案件凶手是一名20年前回到村里照顾年迈父母的63岁男子。在供述犯罪事实时,该男子称其犯罪动机是因为周围邻居排斥他,这使他充满愤怒和怨恨。日本人甚至用“村八分”一词代指这种类型的社会排斥。这一词(字面意思可译作“村八”)是一种可以追溯到日本封建时期的习俗,即日本农村社区居民团结起来,在特定的十种重要场合(如婚嫁、疾病、葬礼、灭火等)上互相帮助。当有人犯下重大违法行为时,作为惩罚,十项事件中有八项禁止向违法者伸出援手。因此,根据普拉索尔(Prasol)的说法,在需要互帮互助的农忙时节,“八项禁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惩罚。被遗弃的人几乎完全被排除在社区生活之外,无法长期生存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社区传统在日本社会开始变得普遍,并成为监管集体行为的基础。
来看一个离我们更近的案例。波士顿校车危机(1974-1988)是一系列暴动事件,这场危机事件的爆发原因是政府规定在波士顿(包括南波士顿、查尔斯顿、西罗克斯伯里、罗斯林德尔和海德公园)传统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社区中废除公立学校的种族歧视。这些骚乱是社区居民对感知到的外部威胁的反应,是一种集体内部团结的体现。迈克尔·帕特里克·麦克唐纳(Michael Patrick MacDonald)在其自传《成长于南方》(南波士顿)中写道:“即使自己是斯皮诺利,社区里的每个个体都声称自己是爱尔兰裔,这是因为生活在南波士顿的大家把彼此都当作家人。我们总会有一种受到保护的安全感,就好像整个社区里的人都在帮助我们提防一些可能的威胁,帮我们注意未知的敌人。没有外来者可以干扰我们。”换句话说,诸如信任和团结这种能将一个团体紧紧团结在一起的精神资源,往往也可以被用于排斥外来者的进入。
波茨提到的社会资本的第二个消极面是对团体成员提出过多的要求。奥德里奇(Aldrich)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群体成员的非正式保险。例如,社会资本使得自然灾害的受害者能够利用预先存在的支持网络来获得财务、信息和情感上的援助。然而,之所以社区成员在他需要帮助时便能在社区网络上获取相应的资源,是因为社区网络上有其他人为他提供了那些资源。而当这个社区已经处于一种资源受限的状态时,互相帮助可能会给团体成员带来过多压力,因为他们经常被要求向他人提供帮助,有时甚至会付出高昂的个人代价。另外涉及双重消极面的例子是,犯罪集团的头领出于其义务,会为他的团体不断扩充成员。黑手党或黑帮等犯罪组织显然是一种社会资本的形式,它们为那些属于犯罪集团的成员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尽管它们对社会其他部分具有负外部性。但即使在这种“阴暗”的社会资本形式下,成员也不能免除过度义务这一负面影响。某日本犯罪集团头目的自传《一个黑手党首领的自白》详细地描述了犯罪网络中的种种义务:当某位黑帮成员进监狱后,集团要为他的家人提供经济支持;支付成员的葬礼和医疗费用;由于自己下属犯下过错而向其他竞争帮派做出赔偿。也就是说,“由于有着如此多的义务,既要好好照看手下,又要保持黑社会的形象,黑社会集团的首领总是缚手缚脚的,而且无论赚了多少钱都不觉得真正够用于组织的维持”。
波茨提到社会资本的第三个消极面是对自由的限制,这种情况通常在一个有凝聚力的群体中存在。如前所述,非正式社会控制有助于减少越轨和反社会行为,但是这种现象的阴暗面会形成一个过度控制和不能容忍多样性的社区。最后,“下降的水准测量规范”(downward-leveling norms)是指团体凝聚力按照团体所接受的规范的方向摧毁离群值的现象。日本谚语“枪打出头鸟”(The nail that sticks out gets hammered down)也许最恰当地表达了这一现象。在教育领域,故意平庸的现象容易在一些较差的学校中发生,这是极其有害的。这种文化观可以看作是这个群体的一个保护机制,即为了确保那些过于努力的学生不会因后来的失败而感到失望。如果学校里的主流规范不是崇尚学术成就,即使是有能力的学生也可能最终与其同伴一样无所作为以寻求认同(例如遵守规范)。杰·麦克劳德(Jay MacLeod)在对“走廊上的游荡者”(Hallway Hangers,指的是在学校的走廊里闲晃而不上课的学生)的经典民族志研究《成功无望》中清晰地描述了这种社会资本的“消极面”。

电影《寄生虫》海报
结型与桥型社会资本
对于研究人员而言,将社会资本区分为结型(bonding)和桥型/链型(bridging/linking)十分重要。在某些特定情形下,这种区分有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资本带来的弊大于利。结型社会资本指在网络或团体中获取的资源,其中网络成员具有相似的背景特征,例如阶级或种族/族裔。从网络术语角度来说,他们是“同质的”。相比而言,桥型社会资本指跨越(或连接)阶级、种族/族裔或其他社会特征而获取的资源。
区分这两种社会资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群体看似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本,但无助于他们维持健康。因此,在许多弱势社区中,较多的结型社会资本成为居民重要的生存机制。但是,如果穷人只有通过互相帮助这一条途径来获得支持,那么他们将永远保持贫困弱势的现状。卡罗尔·斯塔克(Carol Stack)对一个贫穷的非裔美国人社区的经典民族志研究表明,通过亲属关系网络相互支持被认为是“获得(getting by)”的主要机制。这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即它会给集体成员造成经济层面和精神层面上的双重负担。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农村地区的一项研究中,米切尔(Mitchell)和拉果里(LaGory)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他们发现较高的结型社会资本(这一指标是根据具有相同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和关系强度计算得到的)似乎与更多的精神痛苦相关。而对于来自不同种族/阶级背景的人们之间所形成的网络关系(例如桥型社会资本),研究结果则恰恰相反。
以上这些观点可以帮助解释一些研究中出现的不一致结果。例如,在巴尔的摩的一个低收入社区,当母亲对她所在社区的依附水平较低时,其子女的行为或健康问题会更少,也就是说,与社区集体的联系越少,似乎会越有益于健康。齐尔西(Ziersch)和鲍姆(Baum)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一个工人阶级郊区中进行的一项研究也发现,更多的社区活动参与可能会导致更差的健康状况。在对这个社区居民的定性访谈中,他们指出应对和处理由集体互动带来的日常问题会带来相应的压力。除了过多要求帮助他人之外,强结型社会资本往往还表现出波茨列举的所有其他负作用:①规范水平的下降;②集体成员内部一致团结以排斥外来者;③不能容忍多样性,追求集体一致性。
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共识,即在一个弱势的社会群体中,结型社会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中,若不同时增加如经济和人力资本等其他形式的资本投入,仅发展社会资本将毫无意义。
另外,桥型社会资本使得人们能够获得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之外的资源。桥型社会资本明确地将社会资本与权力及资源的结构不平等联系起来。本章开头提到的两个小插曲都涉及了桥型社会资本。在神户大地震的例子中,强结型社会资本(以居民协会的形式呈现)帮助处理灾难的即时性后续事宜(居民之间互相支持,招募志愿者)。相比之下,在漫长的灾后重建过程中,正是新的社会资本的建立(以组织的形式将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社区居民联系起来),才使得人们更快地从灾难中恢复过来。而在印度种族冲突的例子中,印度人民党(BJP)地方分支成员身份增加了印度教徒之间的结型社会资本,穆斯林联盟的成员身份对穆斯林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但这些类型的社会资本自身并没有促进民族和谐。根据瓦什尼(Varshney)的理论,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将两个民族团体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资本。
在不同的情况下,从桥型社会资本中获益的人群也会发生变化。在日本社会,正式组织大多被男性主导(例如,政府机构中女性数量的排名,日本在189个国家中排名第123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相较于男性,女性可能会从桥型社会资本中获益更多。在对日本西部一个中等城市的4000名居民进行的调查中,岩瀬(Iwase)及其同事询问了他们参与家长与教师协会、体育俱乐部、校友会、政治活动俱乐部、公民团体和社区协会这六种组织的情况。作者通过询问参与者与他们所属组织的其他成员的同质性(在性别、年龄和职业方面),来区别结型和桥型社会资本。桥型社会资本(例如,参与成员背景复杂多样的社团)对于自评健康有着较强的保护作用,且相较于男性,这一现象在女性中体现得更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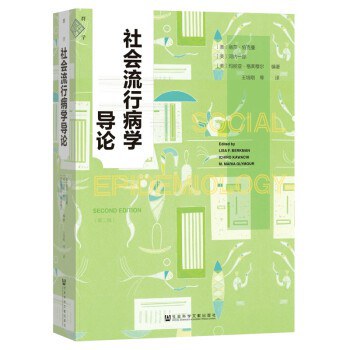
《社会流行病学导论(第2版)》;作者: [美]丽莎·伯克曼(Lisa F. Berkman) / [美]河内一郎(Ichiro Kawachi) / [美]玛丽亚·格莱穆尔(M.Maria Glymou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9月版
注释:
[1] 被称为Machizukuri协会,或字面意思是“社区建设”,最初由居民组织处理附近工厂的污染等问题。后来,他们的职责扩大到处理居民的其他问题,例如改善公园和娱乐空间、预防犯罪等。
[2] 事实上,要解释社会世界的结构和功能是不可能的,除非人们重新引入所有形式的资本,而不仅仅是经济理论承认的一种形式。经济理论允许强加给实践经济定义,这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发明,通过将交换范围缩小为商业交易而实现(布迪厄,1986)。
[3] 来自作者与皇后大学的斯宾赛·摩尔之间的个人交流。我们感谢摩尔博士为本节所提供的见解。
[4] 克里斯塔基斯和福勒曾受到批评,例如科恩-科尔和弗莱彻(2008年)和里昂斯(2011年),更多详细讨论请参见第七章。
[5] 例如,20世纪70年代,在作者(河内一郎)长大的东京邻近社区,每个街角的自动售货机都能买到香烟。很多次,他和他的同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忍不住要花他们的零花钱偷偷地买一包香烟,但他们从来都不敢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在回家之前,他们的妈妈就会发现这件事;一些邻居家长不可避免地会提前打电话来打他们的小报告。
[6] 例如,在2008年的“莱曼冲击”之后,日本政府提供数千美元现金遣返巴西移民工人(《纽约时报》,2009年4月22日)。这些制造业工人——其中许多是有日本血统的巴西国民——得到了现金,只要他们承诺不再返回日本。
【本文节选自《社会流行病学导论》第八章 社会资本、社会凝聚力和健康,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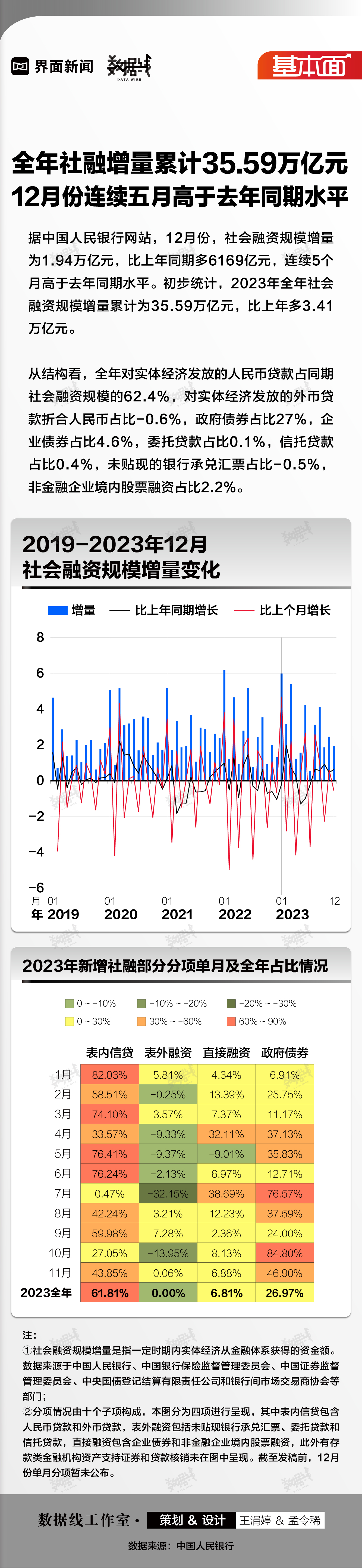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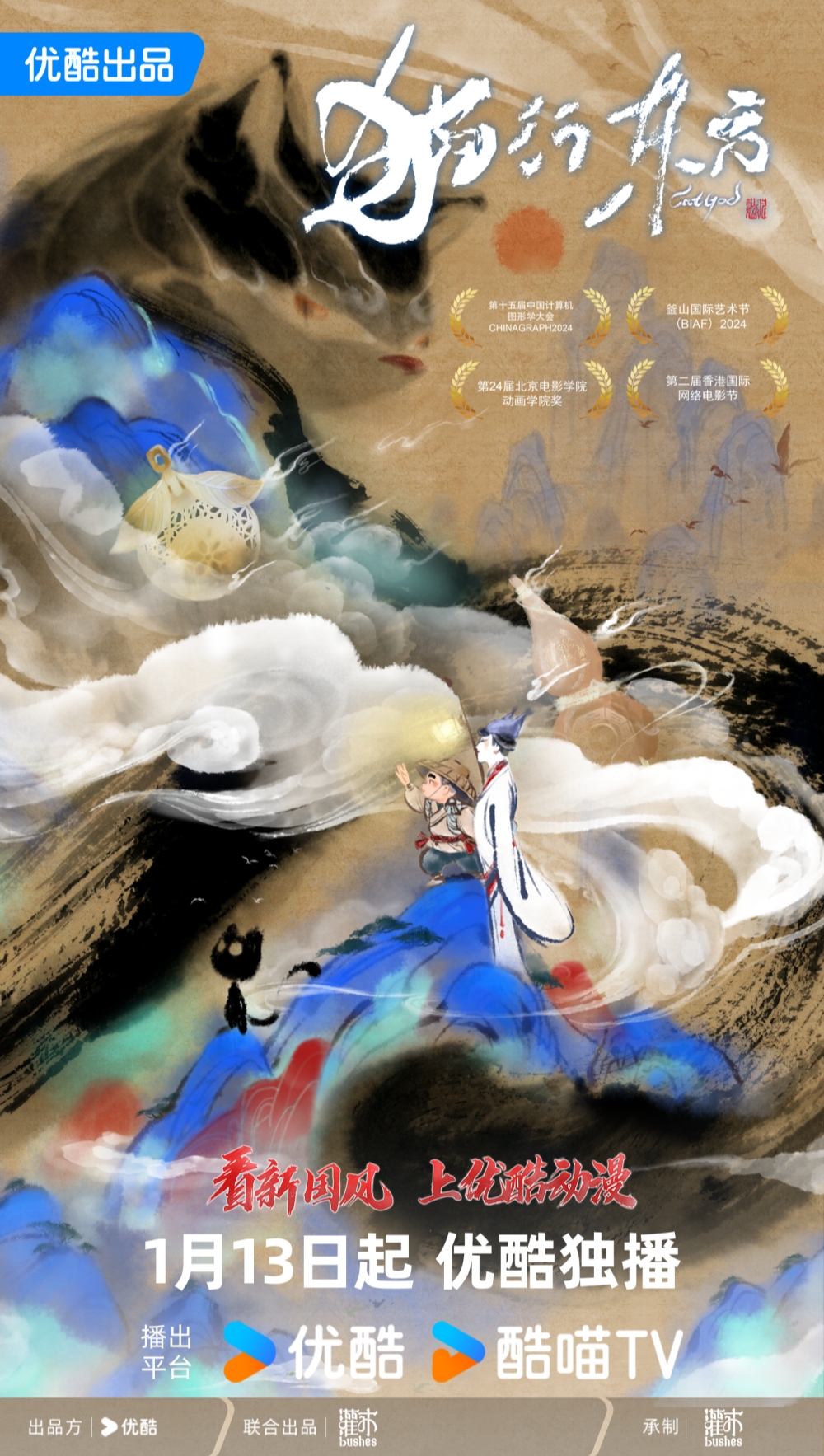
 蜀ICP备2022028980号-1
蜀ICP备2022028980号-1